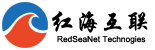《路标》书封。
所谓政治伊斯兰主义,又被称为伊斯兰主义,是一种试图将伊斯兰教作为政治体制和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思想。它和近代以来的基督教政治思想类似,也存在不同分支,而库特布主义则被认为是其中最为保守的支派之一。今天要理解1960年代之后兴起的政治伊斯兰主义,就离不开库布特的著作《路标》。他在该书开篇声称:“人类今天正在毁灭的边缘,这不是由于人们一直担心的毁灭一切的核战,而是因为人性已经失去了那些能让它健康发展和真正进步的关键理念。即使是西方世界也已经发现它不能提供指引人性的健康理念......西方的民主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并且从东方阵营借用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此处指欧洲的福利国家)。”接着,在批驳了西方物质主义福利国家的“衰落”和苏联经济体系的失败后,库特布将他理解中的伊斯兰主义奉为了唯一的替代体系,认为只有贯彻伊斯兰教法才能给人性提供指引。虽然这些文字都是他被捕后在狱中完成的,但其思想在被捕之前就早已成型。
库特布自小熟读伊斯兰教典籍,后来成为了埃及教育部的一名官员,在工作中曾因为理念不同而和政府发生矛盾。库特布还是老牌反对党华夫脱党的成员,华夫脱党是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世俗派政党,主张君主立宪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这个时期的库特布很可能逐渐认识到这类政党的改良方案无力解决埃及各种问题,因而开始转向伊斯兰主义。据称正是由于发现了他的这一转变,教育部于1948年公派库布特到美国留学,希望美国社会的自由风气和教育理念能够让他改观。然而事实上,这次留学很可能反而帮助库特布确立了对于伊斯兰主义的信仰,在偶然中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从他寄回国的信件中,我们得以窥见这些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库特布于1948年的感恩节期间来到了美国纽约,他对于纽约的第一印象是一座“巨大的工厂”。他不仅觉得它“吵闹”,而且将这里的现代城市生活形容为紧张而无趣。1949年,库特布进入华盛顿特区大学学习,在这里他开始感到了乡愁,因为在这里并不能找到能够和他探讨熟悉的文学话题和思想的朋友。在给一位埃及作家的信中他写道:“我多么希望其他人能够谈谈除了钱、电影明星和车模以外的话题。”在他看来,美国人粗俗且缺乏精神生活和美学品味。在他看来,美国人的爵士乐是“嘈杂”的,美国青少年的着装“暴露”且身上往往印着“豹和大象的艳丽纹身”。他将美国人的光鲜时尚称作比尼罗河领域任何事物更为“粗暴”的存在。库特布声称:“高雅文化只能从欧洲进口,然而是美国的大量财富才让它们的发展得以成为可能”。他欣赏根据欧洲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而贬低好莱坞的娱乐类型电影。这种见闻让他得出了对于美国文化的直观印象,即“创造了高度发达物质文明的美国人”所缺乏的正是人的精神价值。

库特布和北科罗拉多大学校长。
同年,他来到了美国中西部的格里利,入学北科罗拉多大学。在此期间,库特布的英语获得了较大提升,他得以融入校园生活并且参加了学校的社团活动。他也为学校的一份英语杂志撰写文章,当时发生的第一次中东战争成为了主题。在文章中他批判西方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还试图向美国同僚展示埃及深厚的精神文化和知识遗产。他写道:“我们曾来到这里向英国人申诉自己的权利,而国际社会帮助英国人反对公正。当我们来到这里申诉自己反对犹太人的权利,国际社会又帮助犹太人反对我们的权利。”在库特布看来,作为二战之后的新兴的霸权,美国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是对拥有悠久文明的阿拉伯国家的践踏,他因此将西方政治和其印象中的野蛮文明联系了起来。
格里利远不如纽约或者华盛顿特区般开放,这座1870年代建立的小城曾是清教徒的乌托邦,它提倡禁酒,并且直到1940年代一直是座道德模范城市。但正是在这座小城里,库特布看到了西方社会的物质主义和道德退化。他认为这座城里的公民都是只关心自身所处的私有领地的人,而“教会则和超市商店招徕顾客一样为了吸引教众互相竞争”。教会的舞蹈也让他不满,他描述道:“人们随着留声机的声音起舞,舞池中到处是诱惑的大腿、紧搂着腰的手臂,紧挨的嘴唇和胸部,这种场景充满了欲望。”他对于西方女性和性的忧虑在这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美国女性在他看来“非常了解她们身体的诱惑能力”并且“并不想隐藏这些”。于是,在这个道德保守的小城里,库特布感受到了道德滑坡的风险,在他看来西方社会早已没有了真正的道德观念,他在日后的著作里称这样的社会为“蒙昧”的。而在其成型的思想中,他将所有缺乏伊斯兰指引的状况都称为“蒙昧”,而将伊斯兰主义作为现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唯一准则来看待。与现代思想家对于非理性状态的理解不同,他认为打破“蒙昧”的并不是现代启蒙理性范式,而是对于伊斯兰信仰的绝对贯彻。
从格里利离开后,库特布又先后来到了加州的旧金山、帕洛阿尔托和圣地亚哥,他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走遍了整个美国。虽然美国人的创造性和组织纪律性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他也更加相信美国现代化的代价是建立在人性价值的缺失和道德以及美学的浅薄之上的。正如有美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库特布对现代美国的看法可以说是一种“西方主义”的卡通式描述,这种印象可能夸大了其面对的文化冲突问题。
如果说库特布对于美国性和道德问题的不满还是出于自身文化传统,那么他对于美国政治的批判就有着时代因素。对于大多数从第三世界来的移民来说,二十世纪的中叶的美国并不是那么友好而理想的,因为当时的美国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种族隔离的社会。同时美国人对于刚刚发生的阿以冲突是站在以色列一边的,库特布作为一个阿拉伯人要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双重边缘化的状况。库特布在书中将美国描述为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并且批判美国白人对于黑人的种族主义态度。例如,他认为格里利这座城市正是建立在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之上的,而且他还相信这种冲突直到1949年仍在进行中。
对于被教育部指派来美国学习的库特布来说,其本身接受新事物的意愿就很弱,而他所接触的美国则恰恰强化了他对于西方乃至现代化的基本看法。有学者指出库特布所批判的西方文明很大程度上正是当时埃及所学习模仿的,因此库特布对于美国的批判更多还是针对的埃及本身。当时埃及的末代法鲁克王朝腐败无能,在对以色列的战争中失败。虽然名义上此前埃及已从英国独立,但是英国一直介入埃及的相关事务。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则由西化精英主导,这些精英尤其是华夫脱党并没有意愿和能力完全实现埃及的独立自主和振兴。库特布虽然也一直反对法鲁克王朝统治,但作为一名传统的保守知识分子,他对西化势力保持警醒并加以批判,并且企图通过塑造一种伊斯兰主义的共同体想象来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通过将美国塑造成为一个“失败”的西化代表,埃及乃至阿拉伯现存秩序的反对者们便拥有了一个形象化的反对目标,即库特布所谓的“蒙昧”的前伊斯兰社会。这对于拥有大量穆斯林和未受教育人口的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来说是一个强大的动员思想,它也促成了穆兄会从与纳赛尔等民族主义者联合转向了独立的伊斯兰主义政治道路。
自美国回国后,库特布就加入了穆斯林兄弟会,开始为穆兄会的理念奔走宣传,成为了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伊斯兰主义者。在纳赛尔带领的自由军官们推翻了法鲁克王朝之后,库特布本有机会加入新政府的内阁任职,但他不仅拒绝更是批判纳赛尔的统治。这不仅是因为穆兄会与自由军官组织的民族主义统一阵线已开始分裂,更是由于库特布认为纳赛尔的世俗统治与古代阿拉伯世界的部落统治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在缺乏伊斯兰指引情况下的“蒙昧”制度。鉴于库特布和穆兄会的影响力,这个保守的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成为了纳赛尔政府的大敌之一,他被两次抓捕并审判,期间还遭受了酷刑折磨,最终以颠覆和煽动叛乱的罪名被绞死。在宣判库特布的审判庭上,日后埃及的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也在场。萨达特时期开启了埃及的全盘西化开放政策,并与美国结盟,他最终被穆兄会的两位枪手所刺杀,而枪手被认为受到了库特布思想的影响。
如果当年埃及教育部没有送库特布游学美国,他是否就不会走向伊斯兰主义?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并没有化解他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疑虑。对于自身文化和制度向来充满自信的美国人往往相信,增进交流必然会促使外人认同其价值观,而库特布的例子却说明了交流隔阂的反作用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都要更大。